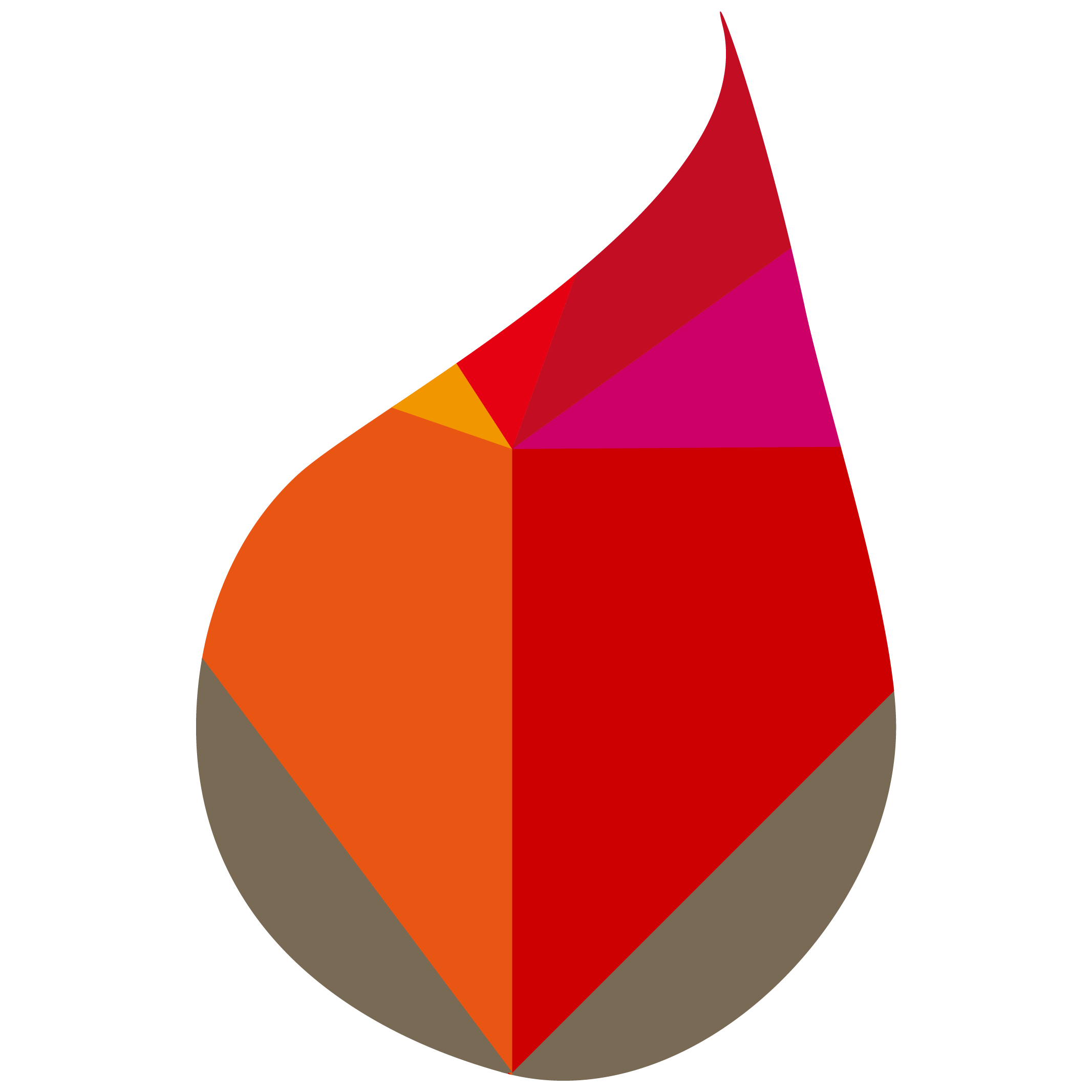W說,「沒辦法,只好下次再死了。」
遇見W的時候,他剛吃了一堆老鼠藥。
W看起來並不特別憂傷。仿佛無所事事,百無聊賴底進行着自殺的俄羅斯轉盤。
W說,他早吃過老鼠藥了,也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。
他輕浮瀟灑,彷彿生命中盡是無可在乎的瑣碎事。
我問W要不要用解藥。
他於是那樣回答了。
W剛從澳洲打工遊學半途而廢歸國。
他說他覺得很煩。
那裡的工作毫無新意,而母國也似乎沒有一絲溫暖。
W是位HIV感染者。
但他身上的氣味並不腐朽。
他拄着點滴架似一盅燃燒的炬燭。
W告訴我,他睡不好。
我問他,那該怎麼辦呢?
他說,那就只好看韓劇了,好好看噢,W這樣說。
且說,他決定要重新好好過生活,並因此網購了一臺iPad給自己。
我大笑着問他要怎麼取件。
W也大笑着回答我,就貨到付款囉!
後來後來,在我離開的那段時間,他也藉故離開了。
再歸來時,他打入了另一場牌局。
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他乃是賭對了底牌。
那幾天我忐忑著總浮現想找他聊聊的念頭,但我始終未付諸實行。
底牌掀開時他贏得漂亮,生命的種種再也撈不着他。
他就如所願底,往死亡靠攏去了。
我問他,你的朋友呢?你的男朋友呢?
W笑說,我沒有男朋友阿!我的朋友們,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在醫院。
我說,叫你的朋友來陪陪你也好阿!
W只是微笑。
我們輾轉聯絡上W的父親與哥哥。
他們並不驚訝,也不曉得那算是冷漠或是釋然。
他們決定放棄他。
然而那只是書面上的字眼,我其實隱約覺得,他們乃是在成全W。
並且透過這樣的儀式,他們得以成全自己的期望以及整個社會的秩序。
我總共認識了W約莫20分鐘不到。
你在那邊好嗎?W。
那邊是不是再也沒有恐懼,
也再沒有關於靈魂的掙扎了。
你覺得很輕很輕,幾乎就要飛了起來
你不要回來了,W。
下一次,你不要再回來我們這裡了。